永不�M足pdf电子书全文在线阅读完整免费版|百度网盘下载
编者语:美国总统特朗普极力阻止发表。作为临床心理学博士的侄女,他亲自揭穿了家族的内幕。
特朗普在本书中直言不讳,充分揭露了她家族的黑暗历史,解释了她的叔叔是如何成为今天的他,以及它是如何间接对全球社会、经济和健康产生巨大影响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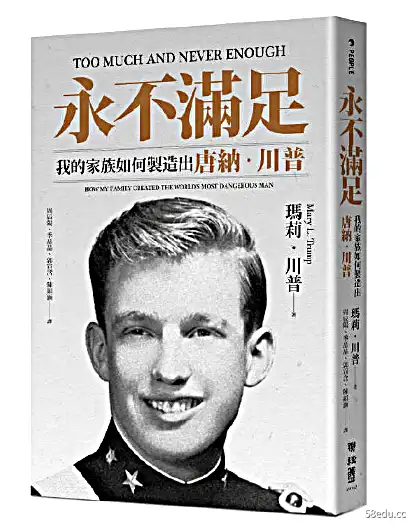
简介
美国亚马逊畅销书No.1
有关该主题的新书在全球售出数百万册
“这是一个家庭失败的悲伤故事。”
成长的匮乏和创伤让狂人的领袖毫无顾忌
特朗普总统强烈阻止发表
作为博士的侄女。在临床心理学中,揭示家庭的内幕
剖析一个功能失调的家庭如何塑造他扭曲的性格
“特朗普的兄弟姐妹都没有幸免于我祖父的反社会人格和我祖母的身心疾病,但我的唐纳叔叔和我的父亲弗雷迪受害最深。他的精神病症状和精神错乱的意义,我们必须阅读家族史。 " “在我祖父的指导、同谋、沉默和对对手的冷漠下,唐纳毁了我父亲。我不能让他再毁了我的国家。” - 玛丽。特朗普引人入胜但也令人恐惧的家庭传奇,特朗普的侄女讲述了这个家庭的故事,描绘了一个混乱而残酷的成长环境。从心理学的角度,揭示了特朗普性格中有太多却从不满足的原因。作为唐纳唯一的侄女,临床心理学领域的玛丽博士。特朗普在这本书中直言不讳,充分揭露了他家族的黑暗历史,解释了为什么她的叔叔会变成今天的他,以及它是如何间接对全球社会、经济和健康产生巨大影响的。
特朗普家族在纽约的豪宅是唐纳德特朗普。特朗普和他的兄弟们共同的成长环境。从她祖父母独特的教养开始,玛丽。特朗普详细描述了这里发生的灾难和创伤,以及老年人偏见、同辈竞争和青少年排斥的扭曲氛围。她还剖析了虐待的父子关系如何造就了疯子首领的独裁,他无法怜悯,不愿表现出脆弱,不愿承担任何责任。
过去,很多假专家和八卦记者爆料批评,试图解释唐纳。特朗普的致命缺陷,但只有玛丽。特朗普有足够的教育和洞察力,再加上亲身经历和圈内人的眼光,让她揭示了特朗普性格发展的真正原因,深入他的内心世界,写下了这个引起全球关注的震撼话题。做。
关于作者
玛丽。特朗普玛丽 L. 特朗普
Derner,美国 Derner 高级心理学研究所,教授创伤、精神病理学和发展心理学课程。他目前和女儿住在纽约。
关于译者
周晨阳
辅仁大学法学硕士,淡江大学美国研究所美国研究组。进入职场后,一直从事国际新闻相关工作。现任联合报新闻部采访中心国际组编译员。
晶晶姬
美国南加州大学公共管理硕士,曾任加拿大RBC银行西温哥华分行助理运营经理。回国后调任编译,包括《价值主张时代》、《从0到1》、《客户反击》等书。
郭宣涵
台中人台南灵魂。毕业于成功大学外国语系和彰化师范大学翻译学院。热爱翻译、运动和美食。合译《穿越荒野:跑步如何使我们成为人类》。
陈允涵
不进办公室,享受长途游牧生活,翻译报纸、杂志和数字媒体的国际新闻编辑。
我的家人如何从不满足唐纳德·特朗普 PDF 预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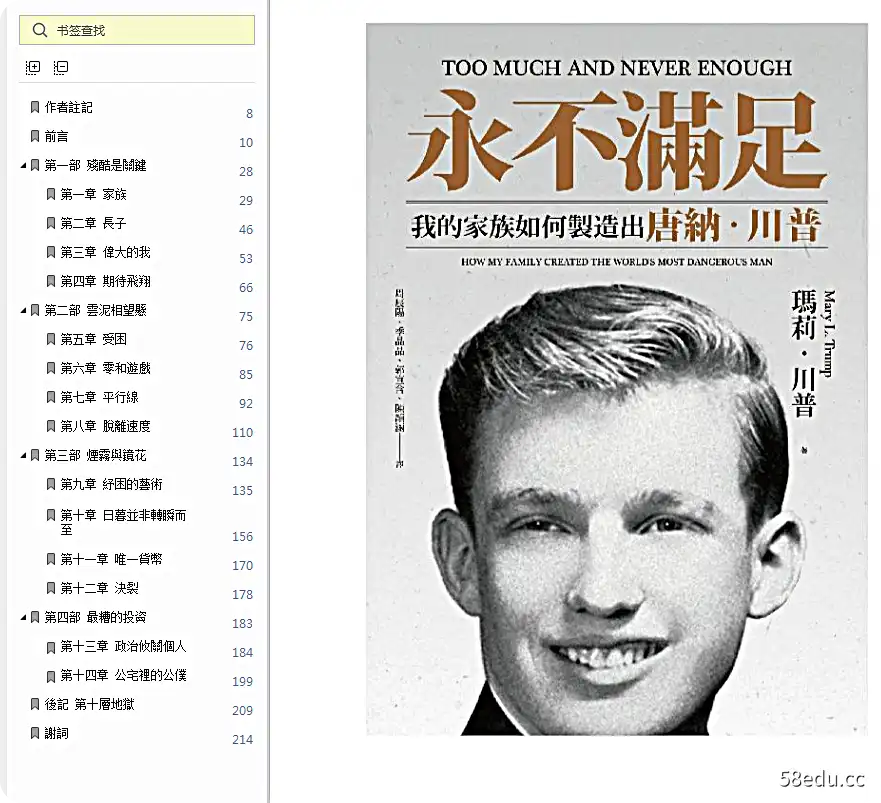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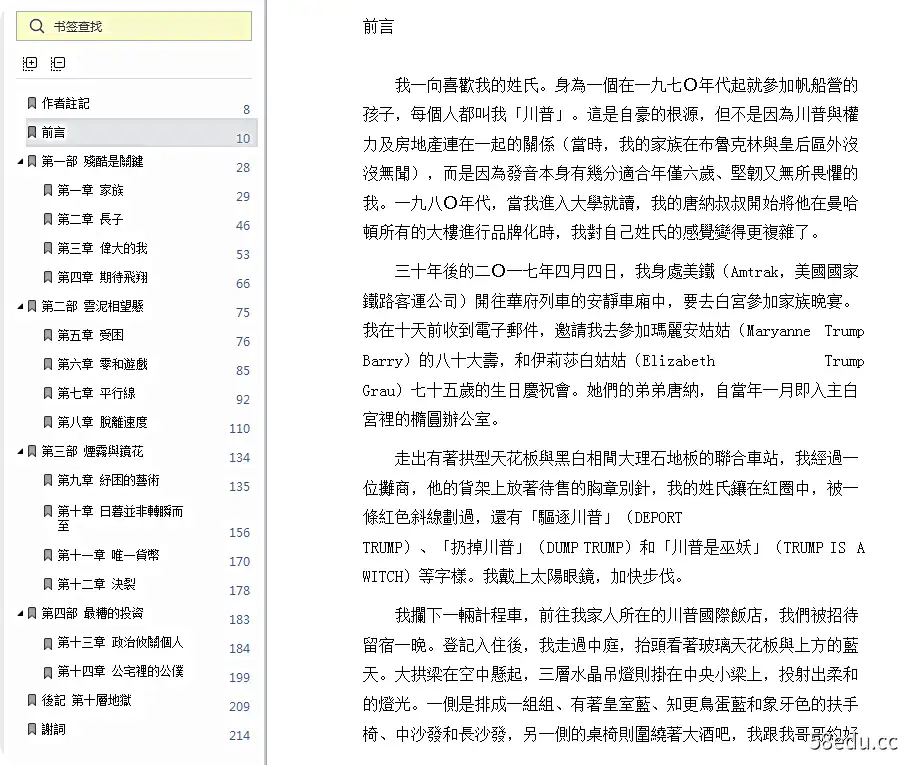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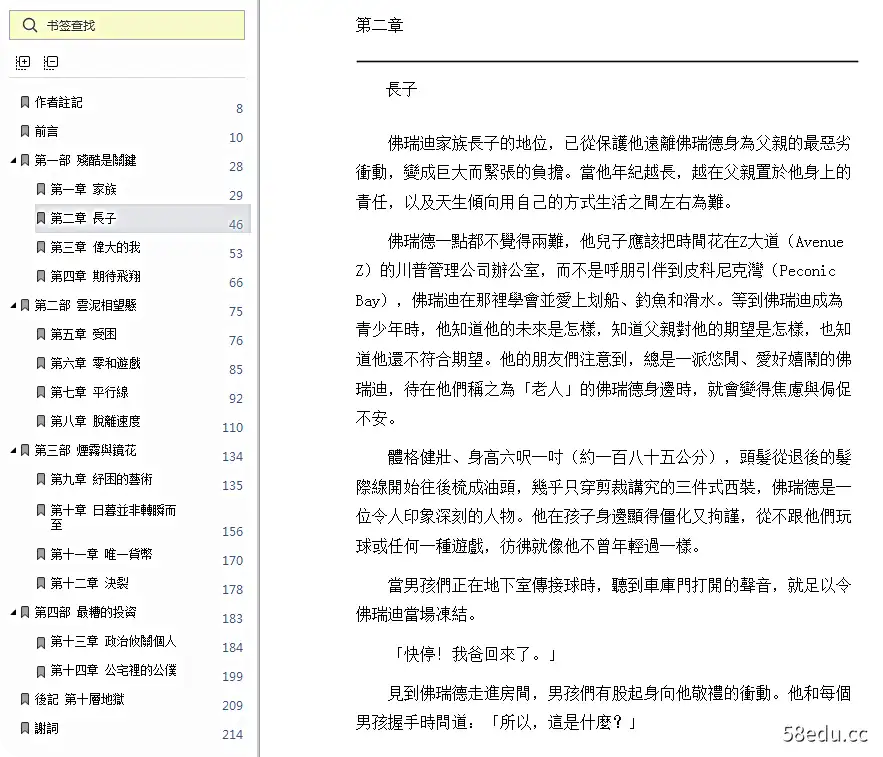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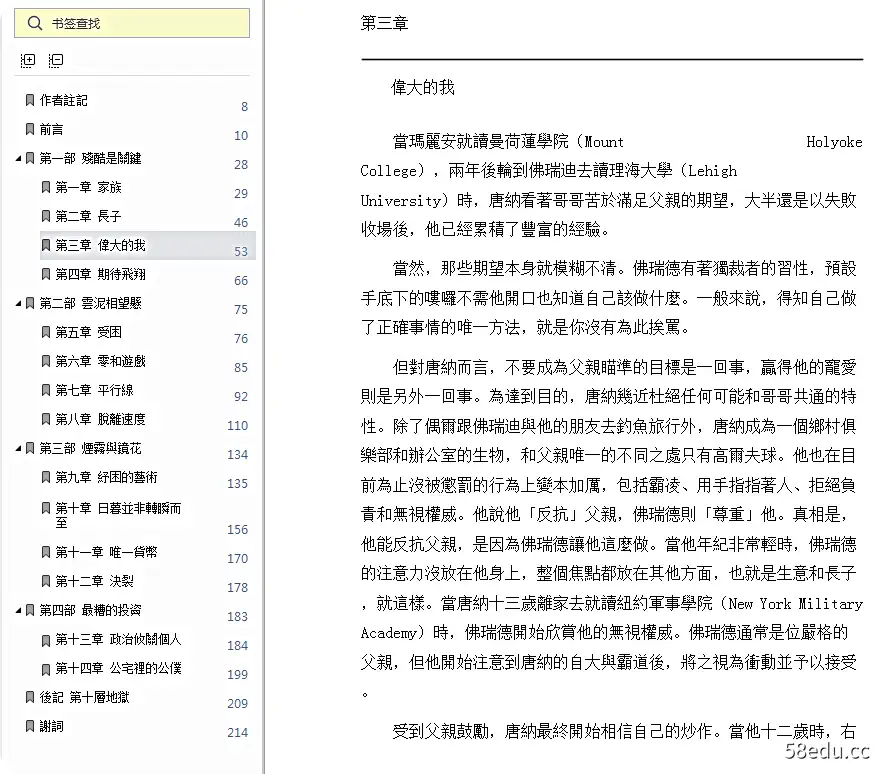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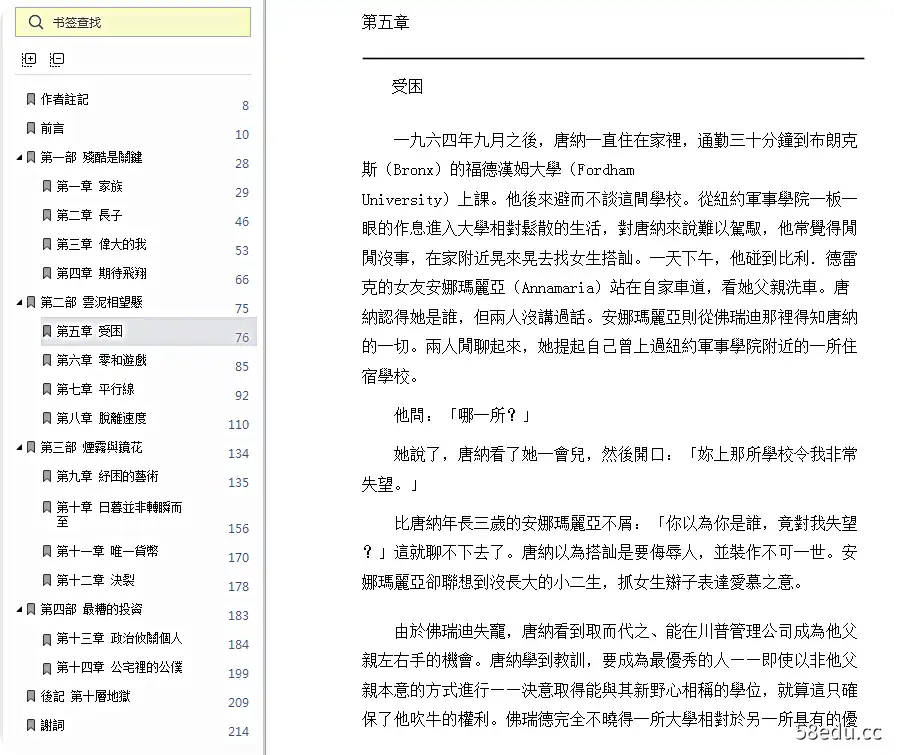
作品目录
作者注
前言
第 1 部分残酷是关键
第 1 章家庭
第2章长子
第 3 章伟大的我
第4章期待飞翔
第二部分云泥悬空
第5章被困
第 6 章零和游戏
第 7 章平行线
第 8 章:起步速度
第 3 部分:烟雾和静花
第 9 章救助的艺术
第 10 章:夕阳并非一蹴而就
第 11 章独特货币
第12章破解
第 4 部分最糟糕的投资
第 13 章政治对个人很重要
第14章酒馆里的公仆
后记:第十地狱
谢谢
亮点
平行线
当弗莱迪(1960 年)和唐纳(1968 年)加入特朗普管理公司时,两人对未来有着相似的愿望:成为父亲弗莱德的得力助手,然后接替他的位置。他们在不同时期以不同方式被培养成接班人,买豪车也不缺钱。但他们的亲密关系到此为止。
弗雷迪很快发现,他的父亲不愿意给他空间,除了最乏味的工作之外什么都不会做,这是在特朗普度假村的建设面临压力的时候必须解决的问题。他感到被困,不受重视,处境艰难,所以他把目光投向了别处。 25 岁时,他成为了一名专业飞行员,在环球航空公司驾驶波音 707 并养活他的小家庭。那是弗雷迪个人和职业生涯的顶峰。 26 岁时回到特朗普管理公司,他的复兴前景被赛道的发展抹去。
在 1971 年之前,除了当了十个月的飞行员外,我父亲为我的祖父工作了十一年。然而,弗雷德将当时只有 24 岁的唐纳提拔为特朗普管理公司总裁。入职三年的唐纳,经验不足,完全没有资格,但弗雷德似乎并不在意。
事实是,弗雷德的特朗普管理层不需要两个儿子中的任何一个。他将自己提升为首席执行官,但职位描述保持不变:他是一名房东。自从六年前的 Horse Park 案之后,弗雷德就没有做过开发项目,所以唐纳作为总裁的工作非常模糊。 1970年代初期,纽约市的经济濒临崩溃,联邦政府削减了对联邦住房管理局的拨款(主要是因为越战开支太高),因此弗雷德无法在那里获得补贴。该州的经济适用房或廉租房补贴计划——米切尔-拉马住房计划——也戛然而止。
就业务运营而言,提拔唐纳毫无意义。他对升职做了什么?我的祖父没有任何开发项目,他几十年来所依赖的政治权力结构正在瓦解,纽约市的财政陷入困境。促销主要是为了惩罚和羞辱弗雷迪。这是一长串惩罚中最新的一个,而且几乎是最无情的,尤其是在那个时候。
弗雷德决心让唐纳坐下。他开始明白,虽然他的二儿子不能专注于细节和每天管理他的生意,但他的性格还有更有价值的东西:敢想敢做。弗雷德一直想将他的商业帝国扩展到河对岸的曼哈顿,这是纽约市房地产开发商梦寐以求的圣杯。他早期的职业生涯表现出自我推销、虚伪和直言不讳的天赋。但弗雷德是第一代德国移民,英语不是他的母语,他必须加强沟通能力——他去了戴尔。卡内基的课程是为他准备的,而不是为了自信。但卡内基课程对他不起作用。另一个障碍,也许更难克服:弗雷德的母亲,虽然有点前瞻性,但总体上是保守的。她的儿子可以成功和富有,但不能炫耀。
唐纳没有这样的限制。他和弗雷迪一样讨厌布鲁克林,但出于一个完全不同的原因——他讨厌工人阶级的无足轻重,缺乏“潜力”,迫不及待地想离开。特朗普管理公司位于布鲁克林南部的 Z 大道,在我祖父的一个大公寓中,位于一栋名为海滩港的大楼内。弗雷德在这里没有进行太多的装修。拥挤的办公室的外层空间塞满了太多的桌子,小窗户没有足够的光线。如果唐纳考虑到附近公寓大楼的单位数量、地租价值以及每个月注入特朗普管理公司的资金数额,他就会发现这是一个巨大的机会。但每次站在办公室外,看着海滩港平淡无奇的外表,他一定是被不配他的想法给窒息了。留在布鲁克林不是他的梦想,他决定尽快离开。
除了由他父亲的公司支付的司机驾驶他从父亲公司租来的凯迪拉克在曼哈顿周围“检查财产”之外,唐纳的工作似乎包括谎报自己的“成就”,据称他还拒绝将公寓出租给黑人(后来成为司法部指控我祖父和唐纳存在种族主义的原因)。
唐纳花费了大量时间在他渴望加入的曼哈顿圈子中树立自己的形象。他是第一代看电视长大的人,每次看几个小时,而且他喜欢专辑。这在塑造他所代表和体现的浮华形象方面发挥了作用。他能够很自在地扮演那个形象,再加上父亲的偏爱,以及提供物质需求的资金,让唐纳有一种莫名的信心,他可以成功地扮演一个起初纯粹是伪装的角色:他不仅把自己被塑造成一个富有的花花公子,同时也是一个极其聪明的白手起家的商人。
早期,那些昂贵的出场都是爷爷私下热情赞助的。弗雷德没有立刻明白唐纳能力有限,无视他的空话,反正唐纳也乐意花他爸的钱。对于弗雷德来说,他决心投资于他的儿子。在 1960 年代后期,弗雷德正在新泽西州开发一座高层建筑作为老人住所,其中一部分是为了获得政府补助(弗雷德收到 780 万美元,实际上一无所获。支付 90% 的利息贷款案件的建设成本),其中一部分突出了他愿意为生第二个儿子做的事情。大楼建成时,唐纳没有支付一分钱,但他收到了咨询费和管理物业的资金,显然是由现场的全职员工提供的。仅此一案就为唐纳带来了每年数万美元的收入,尽管他没有做出任何贡献,无论是开发、进步还是管理,也没有冒丝毫风险。
Fred 使用类似的技巧在拍卖会上以 560 万美元的价格购买了 Swifton Gardens,这是联邦住房管理局的一项计划,最初花费了 1000 万美元。此外,弗雷德还借了 570 万美元的贷款进行清理和维修,而且基本没有为这栋楼支付半毛钱。后来他以 675 万美元的价格卖掉了这座建筑,唐纳拿走了所有的功劳并拿走了大部分利润。
我父亲的飞行梦想被剥夺了,现在连他与生俱来的权利也被剥夺了。他不再是丈夫;儿童很少见。他不知道自己还剩下什么,也不知道接下来要做什么。但他知道,保持自尊的唯一方法就是离开特朗普管理层,而这一次他再也不会回头了。
我父亲搬出高地后的第一套公寓是位于皇后区森尼赛德一条安静的绿树成荫的道路上一栋砖砌联排别墅的地下室套房。他当时三十二岁,从来没有一个人住过。
我们走进去的第一件事就是一个玻璃水箱,里面有两条腰带蛇,还有一个带有球蟒的装饰盒。
在蛇左边的架子上,有一个玻璃缸,里面放着金鱼,另一个有稻草,还有几只小老鼠在里面爬行。我知道那些老鼠是干什么用的。
除了拉出式沙发、一张小餐桌、两把便宜的椅子和一台电视,还有两个带鬣蜥和乌龟的观景箱。我们将它们命名为 Tomato 和 Izzy。
父亲似乎为他的新家感到非常自豪,并不断增加更多的动物。有一次拜访他,他带我们去楼下的锅炉房,看到一个纸箱,里面有六只小鸭子。楼主让他安装一些保温灯,整理成一个临时的养殖房……它们这么小,我们只能用滴管喂它们。
祖父对我父亲说:“想想看,”好像这会帮助他的儿子戒酒,好像这是意志力的问题。他们在书房里,有史以来第一次面对面坐着——不相等,他们从来都不是平等的,但是两个人有一个问题要解决,即使解决方案可能永远无法谈判。虽然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医学界对酗酒和成瘾的看法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公众的看法并没有太大进步。尽管自 1935 年以来,像匿名戒酒者这样的治疗计划就已经存在,但酗酒者仍然在与污名作斗争。
祖父会说:“下定决心,弗雷迪。”他说的是皮尔牧师会赞同但没有效果的陈词滥调。弗雷德最接近哲学的东西是成功神学,他把它用作钝器和逃避,但从来没有像这次那样深深地刺伤他的孩子。
我爸爸说,“他就像告诉我要下定决心摆脱癌症一样。”弗雷迪是对的,但我的祖父全心全意地相信当时盛行的“责备受害者”观点,他无法超越这种心态。
“爸爸,我必须打败它,我想我一个人做不到,我知道我做不到。”弗雷德没有问“我能为你做什么”,而是问道,“你想对我做什么?什么?”弗雷迪不知道从哪里开始。
祖父一生中从未生病;从不错过一天的工作;从来没有因为抑郁、焦虑或心痛而停止,甚至他的妻子也没有死。他似乎完全没有弱点,因此无法理解或同意别人有弱点。
他也不能很好地处理奶奶的伤病。每次奶奶难受的时候,爷爷都会说“一切都很好,不是吗,亲爱的?你只要积极思考就好”,然后慢跑走出房间,让她一个人去处理痛苦。
有时,奶奶会强迫自己回答:“是的,弗雷德。”但她通常保持沉默,咬紧牙关,尽量不哭。我的祖父无限期地坚持一切都“很棒”,没有给其他感受留下空间。
我们被告知我父亲病了,将住院几周。我们还被告知他不得不放弃他的公寓——显然房东想把它租给别人。弗里茨和我去收拾我们留下的衣服、玩具和其他杂物,当我们到达那里时,这个地方几乎空无一人。玻璃罐不见了,蛇不见了。我一直不知道他们的下落。
当我父亲不知道他是从医院还是从疗养院回来时,他搬进了我祖父母家的阁楼。这是一个临时安排,并没有努力将其改造成合适的居住空间。所有的储物箱和旧玩具——包括我祖母多年来藏起来的旧玩具消防车、起重机和垃圾车——都简单地堆放在阁楼的一端,另一端放一张婴儿床。父亲把他的便携式六英寸黑白电视放在窗下的一个旧国民军手提箱上。
Fritz 和我拜访他时,我们在他的婴儿床旁边铺了一块地板,我们三个人看不完的老电影,比如“Tora!Tora!Tora!”这是一个疯狂、疯狂、疯狂、疯狂的世界。如果他足够健康,可以下楼,爸爸会在周日加入我们,观看 WPIX 上的每周喜剧“雅培和科斯特洛”。
一两个月后,我祖父告诉我父亲,他在 1968 年购买的 Sunnyside Towers 中有一个空房间——顶层的一居室公寓。
当她的父亲即将搬到 Sunnyside 时,Marianne 借了 600 美元,准备开始就读霍夫斯特拉法学院。虽然这不是她的首选,但霍夫斯特拉距离牙买加社区只有 10 分钟车程——足够近,她仍然可以早上送表弟去学校,下午接他。重返校园是一个久违的梦想。她还希望成为一名律师能让自己有朝一日离开她的丈夫,她的丈夫多年来变得更糟。大卫的丈夫担任停车场管理员是他永远无法放下的耻辱。多年来,大卫不时向妻子发泄怒火,尤其是在喝醉之后。他的儿子睡在隔壁房间,但不止一次他用枪指着她,用刀威胁她。
Marianne 追求独立让她的丈夫更加疯狂,当她第一天从法学院回家时,她的丈夫一怒之下将他 13 岁的儿子踢出了公寓。玛丽安带着儿子去豪宅过夜。大卫。德斯蒙德清空了这对夫妇的共同储蓄账户并离开了纽约。
当全家人聚在一起时,我们大部分时间都在书房里度过,一个没有书的房间,直到唐纳在 1987 年聘请作家出版《交易的艺术》(The Art of the Deal),才改变了。书架改为展示婚礼和艺术照片。一扇凸窗可以俯瞰后院,对面的墙上是五个兄弟姐妹的成年照片,而不是弗雷迪十四岁时的童年照片。在这里,只有两张在非摄影工作室拍摄的照片。一张是我祖母的黑白照片。她看起来非常高贵,戴着帽子和披肩,和当时还是小女孩的阿姨一起走下来。她出生的苏格兰刘易斯岛斯托诺威的飞机坡道;另一张是唐纳身着纽约军校官方制服带领学校代表团参加纽约市哥伦布日游行的合影。靠墙放着两张两人座的深绿色人造皮沙发,电视机前有一把大椅子,孩子们争先恐后地坐下。祖父穿着三件套西装,打着领带,坐在离门边电话桌最近的双人沙发上,双脚牢牢地着地。
每个星期六,如果我们不在 Sunnyside 和我父亲在一起,我和 Fritz 就会骑自行车沿着 Coastal Land 大道,沿着牙买加社区的后巷到豪宅,和堂兄 David 一起——或者说,这是弗里茨和大卫在一起,我是追随者。
每当玛丽安和伊丽莎白过来的时候,奶奶都会和他们一起坐在一张小桌子旁,桌子上有天蓝色的黑麦莱纳台面,边缘有不锈钢包边,看起来像是 1955 年○ 时代的一家小酒馆。再往前,有一个衣帽间大小、光线昏暗的储藏室,里面有一张小桌子,奶奶用来整理她的购物、收据和账单。可怜的管家玛丽经常躲在那里听她的手提收音机,下雨或太冷的时候,大卫、弗里兹和我不得不在豪宅里,她会被我们烦死的。在储藏室的另一边,有一扇通往餐厅的推拉门。我们会从后门跑到厨房,穿过前厅,绕到餐厅,穿过储藏室,回到厨房,用这条路线作为我们的赛道,互相追逐,推挤,尖叫,加速,一些其中一定会撞到家具。在冰箱和储藏室入口之间,奶奶通常和我们一起冲撞,但如果她在厨房里,她会不耐烦地冲我们大喊停下来。如果我们忽视它,她会用木勺威胁我们——打开抽屉的声音足以让我们服从。但如果有人愚蠢,继续在她身边跑来跑去,大声喧哗,离她最近的人就会被殴打。伊丽莎白尽了她的本分,在我们经过时拉着我们的头发,告诉我们放慢速度。
在那之后,Fritz、David 和我通常会跑进地下室——成年人只经过去洗衣房或停车场,所以我们可以大声喧哗、踢足球、轮流(或争抢)起来在奶奶的电动楼梯电梯里。我们大多在最深处玩耍,打开所有的灯。除了祖父的印第安酋长真人大小的木制雕像,像石棺一样靠墙排列,这是一个相当典型的地下室:带荧光灯的平钉天花板,黑白油毡地板,以及一个古老的立式钢琴的音调太差了,不值得弹奏甚至被忽视。它有唐纳为纽约军事学院乐队戴的大羽毛帽。虽然它会滑到我的鼻梁上,但我偶尔也会戴上它,并将带子系在下巴下面。
当我一个人呆在那里时,那个地下室变成了一个奇怪的异国空间 - 半光,木头印第安人站在阴影中。楼梯对面的拐角处是一个深红色的大酒吧,里面摆着整齐的高脚椅、满是灰尘的眼镜和一个工作水槽,但没有酒——这在不喝酒的人建造的房子里是不寻常的。吧台后面的墙上挂着一幅巨幅画,画的是一位有着美丽丰满的嘴唇和圆润的臀部的黑人歌手。她穿着曲线玲珑的荷叶边金发连衣裙,站在麦克风前,嘴巴微张,双手张开。在他们身后是一个爵士乐队,全是穿着白色晚礼服和黑色领结的黑人男子。喇叭闪闪发光,木管闪闪发光。演奏单簧管的音乐家直直地盯着1、我会站在吧台后面,肩上搭着餐巾,为想象中的顾客提供酒保。或者,我会是唯一的顾客,坐在高脚椅上,想象自己进入了绘画的世界。
罗伯特叔叔比我们大不了多少,更像是兄弟姐妹而不是长辈,每次他从城里回来,他都会和我们一起在后院踢足球。我们玩得像疯了似的,天气热的时候,我们会不停地跑进厨房去拿可乐或葡萄汁。罗伯特经常拿起一块费城奶油芝士,靠在冰箱上,撕下箔纸,把奶油芝士当作糖果吃,然后倒下可乐。
罗伯特是一名非常出色的足球运动员,我尽量不落后于这个男孩,但有时感觉就像他在利用我作为目标。
当唐纳在豪宅时,我们主要是打篮球或通过美式足球。他在纽约军事学院打过篮球,不像罗伯特那么宽容。他不觉得自己应该仁慈,因为他的侄子和侄女只有六岁、九岁或十一岁。当我接住他扔给我的球时,球击中我的皮手套的声音就像子弹击中砖挡土墙一样。即使和孩子们在一起,唐纳说什么都会赢。
只有最勤奋的乐观主义者才能住在 Sunnyside 大厦而不放弃希望。没有门房,亚克力前门两侧的花坛永久地覆盖着一层薄薄的塑料花草。我们六楼的人行道散发着旧烟味,潮湿的地毯是无精打采的灰色,头顶的灯也不够亮,无法隐藏任何东西。
父亲最好的日子是他和我母亲刚结婚的时候,住在萨顿广场附近的一居室公寓里。那一年,他们会和朋友一起去科帕卡巴纳夜总会,然后飞往比米尼度周末。从此走下坡路,反倒是唐纳的生活方式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越来越奢侈。唐纳嫁给伊万娜时已经住在曼哈顿。婚礼结束后,他们住在第五大道的一套两居室公寓,然后搬到第五大道的一套八居室公寓。五年之内,当唐纳是我祖父的受薪雇员时,他们就住在特朗普大厦价值一千万美元的顶层公寓里。
我的祖父在 1960 年代成立了 Midland Associates,以使他的孩子们受益,他们每个人将获得八栋建筑 15% 的股份,其中一栋是 Sunnyside 大楼。这种显然在某种程度上合法的财富转移——如果不是公然的欺骗的话——显然是为了避免对表面上的转移征收大额赠与税。我不知道我父亲是否知道他在他居住的地方拥有部分股份,而在 1973 年,他的持股价值约为 380,000 美元,按当前价格计算约为 220 万美元。他似乎拿不到钱——他的船和飞机都不见了;他的野马和捷豹不见了。他为飞行认证测试(FCT)留下了一个毫无价值的车牌框架,但它现在安装在一辆破旧的大福特上。我父亲曾经拥有的财富在当时纯粹是理论上的。如果他无法使用信托基金,或者他认为他仍然没有使用这笔钱的权利。不管是什么原因,他都得看他父亲的脸。
当对讲机响起时,我父亲和我正在观看电视转播的纽约大都会队棒球比赛。他一脸惊讶,跑去应门。我听不到楼下大厅里有人在喊,但我听到父亲低声说“该死”。下午本来应该是悠闲的,但现在父亲似乎很紧张。他告诉我,“唐纳要来两分钟。” “为什么?” “我不知道。”他似乎很烦躁,这对他来说是不寻常的。
父亲塞好衬衫,铃声一响就打开了门。他后退两步让弟弟进来。唐纳穿着三件套西装和闪亮的皮鞋,手里拿着一个厚厚的牛皮信封,上面缠着几条橡皮筋。他走进客厅。当他看到我时,他喊道:“嗨,小可爱。”我向他挥手。
唐纳转身,轻蔑地环顾四周,对我父亲说:“操,弗莱迪。”我父亲不理他。唐纳把信封丢在咖啡桌上。 “父亲需要你签字,然后带回布鲁克林。” “今天?” “是啊。为什么?你忙吗?” “你拿给他。” “我不能。我要回市中心看看一些需要止赎的房产。现在是利用那些处于高位的人的好时机。”弗雷迪从来不敢独自离开布鲁克林发展。几年前,和琳达周末郊游,开着跨布朗克斯高速公路到波科诺,经过一排排破房子,琳达建议他可以自己创业,翻新布朗克斯的老建筑。
弗雷迪说:“我不能反对我父亲。布鲁克林对他来说就是一切。我永远不会同意。” 。“ “什么?准确的说。”父亲冷笑。
“我不知道。你以前的工作。”
“我曾经做过你的工作。”
唐纳在一阵不舒服的沉默中看着他的手表。 “我的司机在楼下等着,四点之前把这个给我爸,好吗?”唐纳走后,父亲在我身边坐下,点了一支烟。 “所以,小家伙,”他说,“想搭车去布鲁克林吗?” Amy Luerssen 是祖父的秘书和看门人(也是我的教母),在主人的门外有一张桌子。艾米阿姨显然很喜欢我父亲,称他为“我的弗雷迪”。
祖父的私人办公室是一间光线昏暗、四四方方的房间,墙上满是污垢和带框的证书,周围是大量戴着头饰的印度酋长半身像。我坐在他的桌子后面,从似乎无穷无尽的蓝色 Flair 记号笔和像豪宅一样厚的廉价便利贴中挑选出笔和纸来书写和绘画,直到该吃饭了。如果我一个人,我会在他的椅子上疯狂地旋转。
祖父总是带我们去 Gargiulo's,这是一家正式的餐厅,他几乎每天都去那里,有硬布餐巾和桌布。恭敬的服务员认出了他,总是“特朗普先生”和“特朗普先生”的简称,为他拉椅子,在整个用餐过程中始终照顾他的需要。当艾米阿姨或办公室里的其他人和我们一起吃饭时,气氛更好,因为它减轻了我父亲的压力;他和我祖父几乎没什么可谈的。当我们去办公室时,我们不会经常见到唐纳,但当我们这样做时,情况会更糟。他会表现得像他在支配,而祖父似乎不仅鼓励而且享受它。有了唐纳,祖父就变了一个人。
1973 年,司法部民权司指控唐纳和我的祖父违反了 1968 年的《公平住房法》,据我祖父说,该法案拒绝出租黑人 (die Schwarze)。 It was the largest housing discrimination lawsuit in federal history, and the notorious attorney Roy. Roy Cohn offered to help. Downer and Cohen had met at East 55th Street, in trendy, members-only restaurants and disco clubs, the Vanderbilt and Kennedy families, a bunch of international celebrities and family kids. They go there often. Cohen participated disgracefully in Joseph C. Joseph McCarthy's unsuccessful anti-communist movement. He was later forced to resign as the senator's chief counsel, but earlier charges that a dozen people were gay or had ties to the Communist Party had already ruined their lives and careers.
Like many surly but well-connected people, Cohen is not bound by rules. He was beloved by some of New York's upper class and was employed by a variety of clients, including media mogul Ruburt. Murdoch (Rupert Murdoch), gang boss John. Gotti (John Gotti), American lawyer and legal scholar Alan. Alan Dershowitz, and where he grew up, the Roman Catholic Archdiocese of New York. He later became very rich, very successful, very powerful.
While Cohen would show off where Fred seemed conservative, and Cohen would shout where Fred was stern,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was in degree, not type. Cohen's hypocrisy was more blatant, and Fred showed his mastery in his dealings with his family; Fred also trained Donner to be attracted to people like Cohen, just as he would later be drawn to. Authoritarian figures such as Russian President Vladimir Putin and North Korean leader Kim Jong-un are attracted by their willingness to accept flattery and the power to favor Downer.
Cohen suggested Trump Management countersuit against the Justice Department for $100 million, alleging the government made false and misleading statements about his clients. The absurd but high-profile, effective, or at least publicized, operation brought Downer, then 27, to the front pages of newspapers for the first time. And while the counterclaim was dismissed by the court, Trump Management could settle the case. They didn't admit wrongdoing, they just had to change their leasing practices to avoid discriminatory behavior. Because of widespread media coverage, both Cohen and Downer believed a victory had been won.
When Donna relies on Roy. When Coen and his likes made their fortunes, he was supported by the generosity of Fred and the delusional belief that he was gifted and superior. Ironically, the defenses he learned as a child—protecting himself from harm in a childhood full of indifference, fear, and neglect—and being forced to watch Freddie be abused, trained him to develop his brother’s apparent lack of Traits: The "killer" trait and agent ability requested by his father.
It's not clear when Fred started paying attention to Donner, but I suspect it was after he sent his son to the military academy.唐纳似乎很能接受来自他父亲的教诲,要强悍、成为「杀手」,他靠着吹嘘不时被学长痛揍,或假装不在乎自己被家里放逐,来证明自己的价值。佛瑞德对唐纳越来越有信心,他们之间形成一种纽带,且让唐纳有了坚定不移的自信。毕竟,家里最重要的人,唯一讲话有分量的人,终於表现出对他的偏袒。唐纳不像佛瑞迪,他从他父亲那里得到的是正面关注。
大学毕业後,唐纳出社会,用他父亲的人脉去建立更多人脉,也用他父亲的钱打造自己新兴权贵的形象,佛瑞德知道,儿子得到的好评有助於他的利益。毕竟,如果唐纳被视为一个有前途的谈判大师,佛瑞德将厥功甚伟――即使他是唯一知道内情的人。
在一九八○年代早期的访谈,佛瑞德声称,唐纳的成就远超过自己。他说:「我完全放手让唐纳去干。他有了不起的远见,几乎点石成金。唐纳是我所知最聪明的人。」这里面没一句真话,而且佛瑞德铁定在十年前就知道了。
作者:昌杰
链接:https://www.58edu.cc/article/1521776481867411458.html
文章版权归作者所有,58edu信息发布平台,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接受投稿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供广大网友交流学习之目的。如有侵权。联系站长删除。